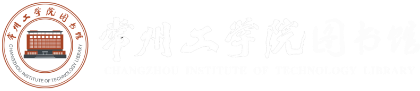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,起身走了
——纪念史铁生
王开岭
北京的园子里,地坛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地方,水泥砖太满,草木受欺,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。尤其盛夏,像抽干了水的池子,让人焦灼。
即便如此,在我心里,仍是器重它的。地坛,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,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。
无论作品或生涯、肉体或精神,史铁生都是和“死亡”、“意义”、“归宿”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,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,我称之为“生命修士”。
疾病,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,在他那儿,却成了哲学,成了修行,成了生命最普通的行李。他让你发现:原来,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,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。
“职业是生病,业余在写作。”他笑得晴朗,像秋天。
一个以告别的方式生活的人,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。
他的从容、镇静、平淡,他健康无比的神色,让你醒悟:焦虑、惊惧、凄愁、急迫、怨愤——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。不应该,也没理由。
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,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他说中了。他注解了自己。
2010年最后一天,上午醒来,我的手机短信最多的,不是“新年快乐”,而是:史铁生走了。
“时间不早了,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;一刻也不想离开你,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。”
他赶上了新年,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,愈发像个仪式。
我并不悲伤,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。它更像个消息,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。
新年钟声响了,在稀疏的报道中,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——
清晨3点46分,他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。6时许,按其遗愿,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。上午,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,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:“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,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,从我们这里走了。他,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,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: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;临走时,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。我自己、我们全科、我们全院、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,都要向他——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。”
那个轮椅上的人,起身走了,几乎带着微笑。
按他的说法,这不是突然,是准时,是如期。
(朗读者:23学前一班 梅如雪)
朗读者介绍
大家好,我是来自23学前一班的梅如雪。我朗读的篇目是王开岭在《精神明亮的人》中的散文《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,起身走了》(节选)。
在书中,结识史铁生、王开岭等人,与之为伍,共沐风雨,隔代相望,是我们热爱生活的重要依据,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。